游戏论·文化的逻辑丨《星露谷物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时至今日,农场模拟经营游戏《星露谷物语》在全球各游戏平台已售2000万分拷贝,制作人Eric Barone说自己在一开始只是想制作一款游戏,复现自己曾经游玩《牧场物语》时获得的感动,2000万的成绩显然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为了不辜负消费者的青睐,他没有就此躺平数钱,而是一直在为游戏制作大小不一的内容更新,这使得现在《星露谷物语》的可游玩内容已经大大超越了其原型《牧场物语》,游戏本身低廉的价格(Steam中国区原价48元),易于上手的特质,优美且暖心的艺术设计和剧情都使得它在发售以来积累了大批粉丝和乐于生产相关内容的网络博主们。
玩家们对于《星露谷物语》的开头可谓再熟悉不过了:你的游戏角色是一名为大公司Joja(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它)卖命的上班族,在“996”里被榨干了对生活的渴望和热情,当你心灰意冷时,你偶然在抽屉里发现一封来自过世的爷爷的信件,信上写着,在一个叫鹈鹕镇(Pelican Town)的神秘小镇上,爷爷给你留下了一座年久失修的农场,等待你在低谷时前往,重振对生命的信心。
就这样,游戏角色逃离大公司资本主义的剥削,前往田园乌托邦寻求本真生活(authentic life)的旅程拉开了序幕,这无疑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压榨的玩家们送上了一贴舒适的疗愈药方。但《星露谷物语》真的如其标榜的,是那样一个免于资本主义污染的世外桃源吗?进入星露谷的线上社区,“如何年入千万”的帖子多不胜数。在玩家间风靡了很久的表情包“我们星露谷玩家是很休闲的”更是道出这款游戏“看似休闲,实则爆肝”的本质。该怎样理解《星露谷物语》中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制作者所描画的生活图景与游戏现实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张力?本文将使用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学概念,通过对游戏机制和剧情的挖掘,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
谁的剩余价值?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笔者一样,第一次游玩星露谷时,每天只是简单地砍柴浇水,精力用完后就回屋睡觉,等待作物成熟。就这样睡过去一年甚至更久,生产规模始终保持在小农经济水平,不知道该怎么快速赚钱。等到稍微查询了一下游戏攻略才恍然大悟,原来要把每天的时间用完!

不得不说这是游戏和玩家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误会。新手以为游戏真的如它所说,提供了多种生产活动,包括耕种,下矿,钓鱼等等,都不必急于求成,享受自己悠闲的农场生活就好,殊不知后期精力根本用不完,真正宝贵的资源是时间。不必笑话玩家的懵懂,在游戏乌托邦语境的暗示下,这一误会的发生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类学家大卫·克雷伯在其名作《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中就提出,尽管我们对现今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但“人的时间可以出售”,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晚近、在前人眼中可能十分荒诞的理念。“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候人们都认为正常的工作模式就是有规律地一阵猛干,然后休息,恢复之后进入新一轮猛干。比如,农活正是如此:农忙时期,调动所有人手,全力投入;农闲时期,大部分时候人们的工作就是些照料和修修补补的活儿,偶尔有些小工程,其余便是到处闲逛了。”这一工作观念发生转变的原因,除了生产力的进步,和人们理解时间的方式的变化有关,钟表的普及使得时间开始控制管理人类哪怕最细微的事务,时间成了和金钱一样需要精打细算、小心支配的有限资产。
任何《星露谷物语》的新手攻略都会首先向你普及游戏的时间系统,一年四个月,每个月一个季节,每个月都是28天,一天可利用20小时(早上6点到次日凌晨2点,超过后系统就会强制玩家睡觉),全年雷打不动,简直达到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完美境界。不过,游戏中并不是所有劳动都需要消耗时间,例如在制作菜单制作物品时,时间是暂停的;当玩家收取作物时,游戏处于间歇性的暂停状态中,大片作物通常只需要一两个小时收取,远低于浇水或耕地的花费。游戏进入中期的标志,就是玩家可以批量制作洒水器,从而省出大量时间用于其他活动。
这一机制并不仅仅服务于游戏性(长时间收取作物会打乱当日乃至整个月的耕种计划),在意识形态上它相当耐人寻味。即使在今天,谷物以外(星露谷中的种植谷物能获得的利润很少),尤其蔬果类作物的采摘仍需要大量人力,是技术一直在尝试解决的劳动密集环节。为何偏偏是在这里,游戏角色既不消耗精力,也不消耗时间?当玩家对着大片的成熟作物望洋兴叹,希望有什么快速收割的方法时,这一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游戏并非没有消耗资源,消耗的只不过是现实玩家的资源,考虑到现代农业不可能不雇佣工人,而星露谷世界的自动化程度并不高,却从头至尾只有游戏角色一人干活的情况,我们可以做出抽象的假设:星露谷世界是现代农业的隐喻,其中的游戏角色(注意它与玩家的区分)实际上雇佣着大量人类劳动力,且以极端夸张的程度购买着他们的时间,获取他们的剩余价值。只不过这一劳动力的集合实际上在游戏之外,也就是玩家本身。在这一最关键处,游戏施展了它的魔力,改写着玩家所身处的现实。游戏角色充当着玩家劳动中介人的角色,将玩家的时间转化为游戏资产,这也是星露谷如此爆肝的根本原因。
星露谷玩家间特有的用以计算某种产品利润价值的概念“每次操作利润”,是指产品卖出后的总利润除以玩家的操作次数。例如啤酒花是比杨桃和上古水果还要赚钱的酿酒流作物,但大部分玩家不会选择,因为它获利要求的操作次数远高于另外两种水果。这表明玩家早就意识到,游戏角色的财富源自游戏之外玩家的辛苦付出。
不过,和现实中不同的是,玩家毕竟认同扮演着游戏中的角色,现实时间转化而来的资产用于把农场建设得更好,也就是劳动力和劳动产品之间尚未发生严重的异化。但必须指出,游戏提供的欲望方程式有其极限,尤其在角色购买了游戏中最贵的物品黄金钟(价值1000万)后,玩家会马上陷入干活不是闲着也不是的尴尬处境,游戏除了资本的自我增殖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外完全无事发生,玩家的异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拼命工作却不知道意义在哪,决定是否该停止游戏的时刻已经来临。
杂货店与超市的市场博弈
作为整个游戏的核心场所,皮埃尔的杂货店与代表大公司资本主义的Joja超市针锋相对。Joja超市的主管莫里斯被刻画为一个飞扬跋扈、不尊重社区价值和商业道德、为了竞争不择手段的人。游戏对玩家的主要驱力之一就是在建设农场的同时为整个鹈鹕镇带来生机,为重建社区中心提供必要的物资,最终齐心协力赶走Joja,重现鹈鹕镇其乐融融的社区氛围。不得不说,这一游戏目标实在有过于田园牧歌和理想化之嫌。
作者通过Joja超市表达自己的资本主义批判并非无的放矢,Joja的手段在现实中早就是大型连锁超商企业的惯用伎俩。例如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3500人小城温斯伯勒曾经有2家百货公司和3家杂货店,沃尔玛入驻该城后,只有1家杂货店活了下来,另一个例外是一家剑走偏锋,只卖沃尔玛没有的商品的商店,为了生存它还不得不削减了员工的工资。
颇有意味的是,尽管剧情花费了大量笔墨体现莫里斯如何长时间使用不公平的倾销手段挤占皮埃尔杂货店的生存空间,但玩家却从来没享受过这一折扣。事实上,除了向日葵种子,疯狂打折的Joja超市所有其他货品都比皮埃尔杂货店贵。想想看,如果玩家购买着Joja超市更加便宜的货品,又怎么能理直气壮地将它赶出鹈鹕镇?皮埃尔就这样利用着制作者的“金手指”,“艰难”地和玩家交易,努力生存下去。很多玩家早就发现皮埃尔并非善类,例如他的高级生长激素单价150,远超过沙漠商店的单价80。在某次更新后,制作者甚至添加了一个专门表现皮埃尔如何坑蒙拐骗的过场动画——他以超高价格向居民们依次出售某件货物,均被拒绝,最后只能希望玩家来买单。肯定有居民会私下抱怨,这卖的比Joja还贵了,要是Joja还在他可不敢这样。


皮埃尔的坑蒙拐骗
没错,Joja并非剧情所倾向呈现的那样十恶不赦。在这个凋敝的小镇上,除了它还有谁能给山姆(兼职)和谢恩提供工作机会(游戏表现Joja邪恶的另一个地方是Joja员工的工资只有每小时5金)?更重要的是,镇长刘易斯不收取Joja税款的行为表示,Joja多半是刘易斯招商引资过来的,利用友好政策吸引大公司为小镇居民提供低价的商品和服务,尽管此举很可能是饮鸩止渴。这一点暗示着刘易斯和皮埃尔之间的利益冲突:玩家在出货箱卖出的货品是由刘易斯收集后转卖给镇外市场的(除了Joja的货车,刘易斯是镇上唯一有汽车的人),是他赚走了差价。游戏确认这一惯例的机制包括,特殊订单“某货物需求量激增”的发布人是刘易斯;当且仅当玩家直接把货品出售给皮埃尔后,皮埃尔才会将其卖给居民,这时居民会有“我买了你刚刚卖给皮埃尔的杨桃,很新鲜”之类的对话。
皮埃尔与刘易斯是鹈鹕镇的上层阶级(如果统治阶级太过刺耳的话),生活条件最为优渥。有人注意到皮埃尔家右下角的小教堂吗?那里供奉着星露谷世界古老的守护神由巴,卡罗琳说是房子的前任主人建造的。如果由皮埃尔决定,那里实际上应该供奉的是金钱本身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近代商业世界创造的新神就是金钱:“金钱就是以色列人的嫉妒的神,除它之外,不允许其他神存在……金钱是人的工作和存在的异化的本质;这个本质支配着他,而他崇拜它。”
鹈鹕镇的暗面
游戏时间的第二年春天,乔迪从战场回来的丈夫肯特会到农场拜访,向你表示友好。他的回归预示着鹈鹕镇的阴暗面正在玩家面前缓缓揭开,此时玩家终于弄清楚了礼物与友好度系统,可以解锁一小半居民的爱心事件,我们得以看到居民们各不相同的沮丧和烦恼。
首当其冲的就是肯特的Ptsd场面,因为妻子做爆米花的声音让他回想起枪林弹雨,肯特失控了。尤其引起笔者关注的是镇上年轻人们的内心状况,他们过得开心吗?除了莉亚和艾利欧特这两个外来艺术家外,其他本地年轻人的生活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璀璨,玛鲁在哈维的医院打工,艾米丽在格斯的酒吧打工,潘妮在博物馆教书,只有贾斯和文森特两个学生,亚力克斯不可能在这里找到他希求的运动员生涯,塞巴斯蒂安希望攒钱去大城市,每天在家里接编程的零活,而想想主角是从大城市来到这里寻找本真生活的,塞巴斯蒂安这一选择就更加意味深长。如果一个地方无法为年轻人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那么它何以成为一个理想乡?
“刘易斯之罪”因此显得令人难以饶恕,玩家根据秘密纸条#19的提示找到的“刘易斯黄金像”说明刘易斯的敛财行为已经到了夸张的程度,可这样的他却把“如果你们这些孩子把找复活节蛋的热情拿来捡垃圾,鹈鹕镇早就是宝石之海一带最干净的城市了”挂在嘴边,不愿意请人打扫小镇;他对潘姆、潘妮母女住在房车里的情况保持沉默,最终竟然是玩家出钱给她们盖房子。
刘易斯的利益顾虑是他和玛妮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却不能公开恋情的原因,由此也引发了玩家最爱梗“刘易斯的紫内裤”这一剧情,制作者也十分会心,让紫内裤在展览会和夏威夷宴会上都有对应剧情。刘易斯对低调的过分坚持是担心自己像莫里斯一样在事发后被公开抵制,失去上流地位,这样皮埃尔就在竞争中胜出了。
姜岛的殖民隐喻
《星露谷物语》的1.5版本免费更新体量十分庞大,包括一个资料片级别的新地图“姜岛”和一系列的新道具新挑战。从玩家的角度出发,没有任何理由不为这次更新感到开心。需要花费20个金色核桃解锁的姜岛农场,更是有着超大的耕地面积,且一整年四季如春,铺开上古种子后永远不会枯萎,简直就是苦于农场地方太小的玩家的天堂。
“酿酒流”玩家多半都会做同一件事,就是把种植上古水果彻底转移到姜岛(和温室)上,把自家农场的宝贵土地腾出来,或者是疯狂盖小屋放置酒桶,或者是搞“自我实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使用丰富的道具,在农场里建电影院、水族馆、餐厅等休闲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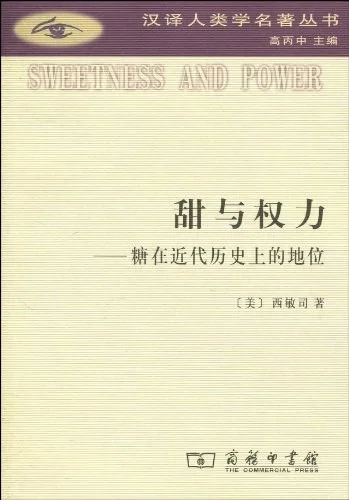
是的,玩家对姜岛所做的,是不折不扣的殖民行为,它很清晰地体现了资本为了增长向外寻求更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的发展趋势。尽管姜岛上仅有的几位NPC都不会为我们工作,但不要忘记上文的分析,玩家再次充当了游戏主角需求的低廉劳动力,且这一剥削更胜从前,每次姜岛作物成熟,真是让玩家又开心又发愁。殖民历史上,廉价劳动力和肥沃的土地一样吸引着宗主国。人类学家西敏司在《甜与权力》中追寻了糖从奢侈品转化为标准工业化商品的过程,17-18世纪,西方国家纷纷将甘蔗的种植和灌溉,糖的提纯和精炼转移至加勒比海地区,依赖当地劳动力维系糖这一劳动密集的生产链条。西敏司认为,这一流畅运转,环环相扣的生产体系,实际上就是工业化的雏形。
准确来说,姜岛至少叠加着三个时空的殖民/殖民性行为,除去种植和收获作物外,雷欧这个狼孩(或者说“鸟孩”)“归化”的剧情体现着宗主国如何通过对他者的教化界定自身文明的优势和主体性,虽然制作者选择了较为折衷的办法,也就是让流浪汉莱纳斯这一坚持不进入主流社会的角色充当雷欧的导师。姜岛度假村的发生条件更加现代,现实中,异域之地要具备风情,需要颇多的硬性条件,“文明国家”血腥的殖民行为被温情的全球化所代替,当地人在田野里大汗淋漓的劳作被外包的工厂和客服中心所取代,异域既不是完全原始的,又不是彻底城市化的。如何引诱出游客的好奇心,让其在探索时不遭遇令人愧疚的历史现实,是现代“风情”旅游业必须学习的一课。
自动化的意味
在自动化之路上,《星露谷物语》走得相当谨慎,1.3版本加入的自动采集器可以自动收集畜牧业初级的动物产品(包括牛奶,羊毛,鸡蛋等)。1.5版本加入的自动抚摸机可以每天代替玩家抚摸一次动物,提升动物友好度,最终提高动物产品的品质。动物友好度与产品质量的关联被粉丝视为星露谷“人味”的一大体现,玩家关爱动物,动物则回馈玩家。制作者此举也招来了不少非议,可考虑到畜牧业的鸡肋处境,自动化又是势在必行。早就有“星露谷经济学家”用数学工具计算出畜牧业利润微薄,尤其绵羊需要不低的解锁条件,回本周期却超长,根本不值得饲养。更有甚者后期直接卖出所有动物,在畜棚里放满酒桶。如果制作者不提供每日采集和抚摸的解决方案,玩家们恐怕会直接跳过这部分游戏内容,毕竟,大部分玩家从未真正将畜牧业的动物视为自己的宠物。
玩家在畜棚中放满酒桶
即便是这样,制作者仍为两种机器设置了许多限制,比如自动抚摸机只能提供玩家亲自抚摸一半的友好度,且只能在骷髅洞穴的宝箱中低机率开出(抚摸机的物品说明还指出这一产品是Joja公司的邪恶发明);自动采集器无法采集畜牧业最赚钱的松露,必须由玩家一个个手动拾取。畜牧业之外,1.5版本在姜岛“齐先生的核桃房”中用珍稀货币齐钻购买的加料机无疑是在玩家间大受欢迎的自动化mod(automate)的超级劣化版,自动化mod可以仅用一个木箱实现一整条生产线的自动化,如自动收集虫饵盒制造的鱼饵,将鱼饵自动添加到蟹笼中,又自动收取蟹笼捕获的水产。加料机却只能自动向一台机器添加原料,且无法自动收取产品。
其实,制作者对于自动化的忸怩态度,本身就暴露了农场模拟经营类游戏以田园生活对抗资本主义这一叙事的内在矛盾。为了给玩家提供持续不断的快感反馈,游戏以采菊东篱下的诗意外壳包装着生产至上的实质,本该怡然自得、清静无为的乌托邦里实则处处浸润着增长与扩张的神话。当制作者以丰盛的游戏更新吸引着全世界玩家,留旧迎新之际,农场生产力水平的上涨并非来自技术水平的飞跃,而是玩家越来越高强度的劳作投入,甜蜜地痛苦着的玩家内心早已不堪负累。自动化成了制作者“不得已而用之”的凶器,它减轻了玩家的劳作负担,却是对整个游戏世界田园灵韵的祛魅。
即使是休闲游戏的另一座半壁江山《动物森友会》也未能跳出这一内在矛盾,它巧妙地用无期限借贷转移了增长对玩家的异化,还款只是为了住更大的房子。其实住小屋也没什么不好,只是玩家为了美化自己的家园,获得更多的可自定义空间,依然会去开心地挣钱还款。游戏发售初期的“高价大头菜岛屿”才会那样地一票难求。说到底,现实世界贷款去小岛拓荒又怎么能如此悠闲浪漫?游戏在此处又大展幻术,玩家经历的,只是被凝结在还款前的“刹那永恒”而已。
和大部分游戏制作人相比,《星露谷物语》之父Eric Barone不必担心资金流问题,不必应对投资者的无理要求,已经算足够幸运。我想他比任何人都希望保持游戏的初心,但就像游戏后期很多玩家会全天保持烹饪物品“三倍浓缩咖啡”和“香辣鳗鱼”提供的速度增益效果一样,制作者希望玩家沉醉在慢生活中不愿离开,把这个世界做得越来越大,无边无际的慢生活却给玩家以焦虑感,让ta不自觉地呼喊着“快,还要更快”。于是,在游戏真实(truth)将要溢出其现实之际,为了防止《星露谷物语》演变为《异星工厂》(Factorio)或《环世界》(Rimworld)这样的“工科模拟器”,制作者只得动用自己的造物主之手,为游戏划下不可雇佣和低自动化的底线。
《星露谷物语》充满张力的游戏体验提示着我们,或许欲望机器的周转不灵和田园美梦的破产对于玩家而言是有着批判性意味的积极经验。购买黄金钟后紧随着成就感而来的失落让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肝,以及最终又肝出了什么。




